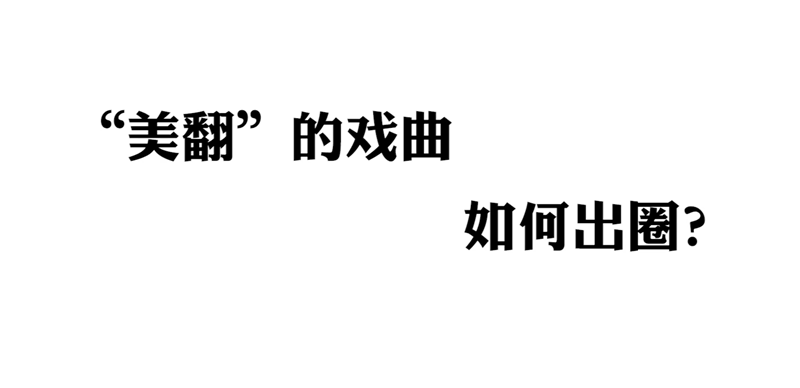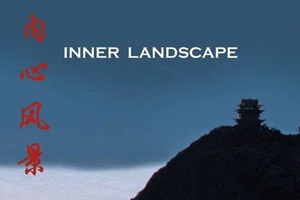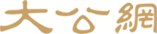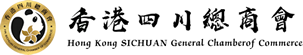觀演:從觀眾心理出發的表演策略
采訪人:張之薇
受訪人:沈鐵梅
Q&A
張之薇:我也注意到沈福存先生的《鳳還巢》《玉堂春》《王寶釧》《春秋配•拾柴》這些代表作皆為傳統戲,但是,在這些傳統戲中他並非一味模仿前人,而是有自己獨特的演法。更重要的是,他對傳統戲的創新不僅博得了戲迷觀眾的認可,也博得了業界人士的認可,這很不容易,您覺得他抓住了什麼?
沈鐵梅:我覺得之所以我父親在20世紀80年代後越來越獲得觀眾和業界的認可,是因為他不僅站在戲曲規律的角度、站在演員表演和塑造人物的角度去創造,同時也是站在觀眾的角度去創造。

京劇《白蛇傳·遊湖》 沈福存 飾 白素貞(右)
實際上,在戲曲表演中,不可忽視的是總會有兩個“我”存在著,一個是作為演員的“我”,另一個是作為角色的“我”,戲曲演員是在這兩個“我”之間跳進跳出穿梭著的,同時也是這兩個“我”在與觀眾交流。戲曲的欣賞接受,實際上就是在內化、外化的不停轉換之間形成一種觀演的心理,觀眾不僅是在看劇情,實際上更重要的是,觀眾還在為演員的表演、演員的技術叫好,這是與西方戲劇的表演不太一樣的地方。父親令我叫絕的是,他能夠從觀眾的角度和自身的角度去傳遞他的表演,換句話說,他知道觀眾想看什麼,並能自如地做到,這其中包括技法、唱腔、身段,甚至眼神、腳步,這種具有明確引導性的表演在我父親這裏是很明顯的,也因此,在舞臺上他總能通過對人物內在的塑造引爆觀眾一片叫好聲,專家內行稱之為“沈氏觀演心理學”。比如:在我父親的表演中,他會通過一個戲曲的小跳步來表現人物的年輕態,人物的感覺立刻就不一樣了。

京劇《玉堂春》 沈福存 飾 蘇三
現在的戲曲舞臺,有的時候演員會脫離人物去賣弄技法,有的時候舞臺上僅僅是演員與演員之間的交流,有的時候更多是以民間舞蹈或群舞的方式展現,這是對“以歌舞演故事”這句話的曲解,如此反而遮蓋了主演表演的魅力。我認為,中國戲曲的魅力一定不能忽略觀眾這一方,即觀眾欣賞的參與。演員通過表演的停頓、內化、外化等方式,讓觀眾領會、欣賞、被感染,兩者形成一種流動,這是一種觀演美學。觀與演的密切關系在戲曲發展中是很重要的,這也是當前戲曲創作尤其是現代戲創作所忽視的。
在戲曲表演中,觀與演的關系是必須要重視的。演員是舞臺主體,只是演員該以怎樣的方式來展現自己的表演呢?父親常常會告訴我,要講究分寸的把握。什麼是分寸?不僅要避免孔雀開屏式的表演、避免“灑狗血”,而且在唱腔設計方面要避免太多過高的上行腔設計,要將這種腔用在刀刃上。演唱時,要注重高低腔的對比,運用低音、輕聲來傳遞人物的內心,通過聲腔把控、眼神和腳步的配合來吸引觀眾注意力,這是父親一整套實踐總結的結果。比如:在川劇中有很多無伴奏徒歌的演唱段落,這就是以靜制動的體現。對分寸恰到好處的運用,既對演員有益處,也是抓住觀眾注意力的一種策略。藝術分寸也包括整體舞臺效果這個層面,還包含一臺戲主演與配演的合作,以及主演與樂隊之間的默契程度。戲曲是一門每個環節都需要恰到好處、分寸銜接的藝術。
Q&A
張之薇:您能具體談一下您父親在自己的旦行藝術中是如何把握女性的分寸感的?
沈鐵梅:比如水袖是旦行演員很重要、也是很見功力的一種技藝,它不僅有動律之美,而且還可以傳情達意, 是有豐富的語匯內涵的。我父親在《玉堂春•嫖院》一折和在《鳳還巢》“在簾內偷覷郎君”一段中,同樣運用翻袖動作,卻是大不同的。這是因為蘇三和程雪娥這兩個女性身份、地位的不同,以及隨角色情緒的不同而變化的。前者是對愛情憧憬的妓女蘇三,後者是面對異性嬌羞的大家閨秀程雪娥。兩者不一樣幅度的翻袖,前者配以小跳,後者沒有小跳,這不一樣的腳步方式,皆是揣摩角色變化之後的一套法則。

京劇《節烈千秋》 沈福存 飾 張春姑
眼神也是父親在戲曲表演中非常重視的一點。父親常常教我,當女人看男人的時候,要先耷眼皮,由下往上看,對眼神、再耷眼皮,對眼前人表現出先羞澀、後思索、再轉身與觀眾交流,這一系列眼神的躲閃、對眼睛的遮擋、然後再回望的動作銜接其實是對生活的誇張和提煉,也體現出女性特有的情態,而不是一見男性就馬上露出笑臉,這種表演就不是古代女性了。所以,在舞臺上對性別的強調是對生活細致觀察的藝術化表現。而這些都是在戲曲規律內的創新,可謂平淡中見波瀾。
因為父親是一名旦行演員,所以陰與陽、雌與雄的不同美感在他的腦子中是很明確的。作為男旦,如何將劇中女性人物的陰柔之美和自身男性的氣質恰到好處地調和在一起,他是經過思考的。旦行中的青衣,端莊穩重,從前皆是演員抱著肚子唱,觀眾閉著眼睛聽,其規範是嚴謹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突圍也是很難的。但是,父親的表演總是能在准備和蓄勢之中突然給觀眾放一顆“原子彈”,讓劇場效果熱起來。比如:他的《玉堂春•三堂會審》中“十六歲開懷”一段,他用玩弄自己的發辮、綢條和手袖遮擋來表達尷尬、糾結、難言的羞澀,與前人是不一樣的效果。《春秋配•拾柴》中薑秋蓮借乳娘的“幾問”,在情緒、身段、唱腔、心理上層層遞進,有很好的劇場效果,但是他又絕不會讓自己的表演太滿,這就是一種對表演尺度的把控。這些其實都滲透了父親對人物的理解和對戲曲審美的思考。

京劇《春秋配•拾柴》 沈福存 飾 薑秋蓮
Q&A
張之薇:也就是說,沈先生的這些作品雖然皆是傳統戲,但是卻很大程度上演出了新意,演出了大不同,劇場效果也很不錯?
沈鐵梅:對,作為土生土長的重慶人,父親常年浸潤在川劇的環境中,他常和我說他非常喜歡我唱的川劇《思凡》。他究竟喜歡什麼呢?其實,他看到了川劇中很重要的一個特性,那就是趣味性。他常常有意識地把這種趣味性移用到自己的表演中。比如:《玉堂春•監會》中王金龍來探監,“三賠禮”這一場戲——一賠禮,王拍肩,蘇三用手拿下;二賠禮,王摟肩,蘇三抖肩;三賠禮,我父親在表演這段時,為了表達對情人王金龍的委屈和怨,采用了光動嘴卻不發聲的小動作,很好地表達出一種愛恨交織的情趣。這其實是從川劇中借用過來的表演方法,原本在京劇中並沒有。這樣的處理常常引爆劇場。這種帶有生活氣息的層次感,實際上是我父親結合生活經驗之後對角色塑造的再思考。包括在《武家坡》中,王寶釧和薛平貴進入窯門後,薛平貴起身時,王寶釧很自然地用水袖替丈夫膝蓋撣土的動作,也是充滿趣味性的。

川劇(高腔)《思凡》 沈鐵梅 飾 色空
Q&A
張之薇:那麼這種在沈先生表演中的趣味性傾向,您覺得與重慶這塊地域有關系嗎?
沈鐵梅:我認為,只要是人都是喜歡趣味性的,關鍵是創作者能不能找到恰當的手法去呈現,而且找到的手法是不是准確地表達了人物。在我的戲的創作中,父親為我打磨時都會提到川劇的趣味性問題,我相信父親一定是站在表演者的角度、站在觀看者的角度,深悟了藝術趣味性的重要。人們一般會認為趣味直接與喜劇相關聯,而與悲劇和正劇無關,但是,實際上在戲曲中並不是如此。再正的戲也一定要有俏頭,就好像我們在炒菜時放的調味劑。在川劇中,悲劇一定有喜劇性情節穿插其中,而喜劇也一定有悲劇性因素穿插其中,川劇就是在悲喜的起起落落之間完成的。比如:川劇《打神告廟》本身是一個悲劇,這毋庸置疑,但是其中的兩個皂隸形象是由人來扮演的喜劇形象。他們的唱詞極具民俗性,加之模仿木偶的動作表演,呈現出川劇的趣味性,而喜劇形象的摻雜則是為了襯托焦桂英這個人物濃烈的悲劇性。
在京劇青衣這個行當中,觀賞的時候更多會有沉悶的氛圍,但是父親的表演卻總能通過一些細節的創造性挖掘讓只唱不演的人物一下有了生命力,更加打動人。父親是真正的大青衣,他表演的趣味性是有分寸的。文戲中的趣味性相對來說更雅致一些,絕非我們常常說的插科打諢這一層面的趣味,所以,父親在表演時的趣味性絕不是俗趣,而是一種雅趣,這是一種度的把握,可以表現在眼神動作上,也可以表現在唱腔、整體節奏的一氣呵成上。比如《春秋配•拾柴》,這樣一個平平無奇的“歇工戲”,在家父的演繹下無比精彩,特別是在“三問”的處理上、與乳娘的配合上有他自己的一套演法,賞來令人忍俊不禁。這也是這樣一出戲能夠成為他的代表作的重要原因。(來源:《中國文藝評論》2024年第5期)

父親沈福存(右)、恩師競華(左)與沈鐵梅(中)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