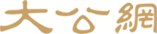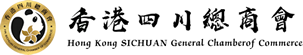圖:乾隆皇帝曾敕令繪製《毛詩全圖》資料圖片
(一)
清乾隆四年(公元一七三九年)春天,二十八歲的乾隆皇帝下了一道諭旨,敕令畫院諸臣辦一件大事,那就是依照南宋畫家馬和之《詩經圖》筆意,繪製一幅完整的《毛詩全圖》。
馬和之是南宋時代的經典畫家,距離乾隆很遠,遠得連他的生卒年份都打聽不到。宋末文人周密曾說:「御前畫院僅十人,和之居其首焉」,意思是說,南宋王朝的皇家畫院只有十個編制,馬和之的級別最高,足見他在宋高宗趙構心裏的地位。這一君一臣,成了美術史上的絕佳搭檔,馬和之繪圖,宋高宗寫字,成了他們合作的經典模式。比如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著名宋畫《後赤壁賦圖卷》,就是二人合作的結果。馬和之與宋高宗,南宋初年這兩位藝術超人,猶如舞者與歌者,舉手抬足,配合得天衣無縫,那默契,不是演練來的,是骨子裏的。
《詩經圖》,依例是馬和之繪圖,宋高宗寫字(即《詩經》原文),後來宋孝宗補寫了一些。《詩經圖》採取左詩右圖的形式,詩圖並茂,彼此相映,成為美術史上的不朽之作。二○一五年秋天,我站在故宮博物院延禧宮的展廳裏,面對這幅《詩經圖》流連不去,心裏想起明代汪砢玉在《珊瑚網》裏對馬和之的誇讚:「不寫宣姜侄事,但寫鶉奔鵲疆,樹石動合程法,覽之沖然,由其胸中自有《風》《雅》也。」
六百多年以後,這一組《詩經圖》落在乾隆的案頭時,已然只剩下了一些殘卷。這些殘卷包括:《豳風七篇》、《召南八篇》、《鄘風四篇》等,一共九件。
這讓乾隆很不甘心。他一面摩挲着這些古畫,一面在內心深處努力復原着一部完整的圖文版《詩經》。乾隆有嚴重的強迫症,他不接受殘缺的事物。他要向時間討債,讓時間歸還那些被它沒收的部分。這才有了前面提到的那道諭旨,讓朝廷畫院裏的臣工們,共同補畫那些散佚的部分。
(二)
我猜想那時分,宮殿裏一定是春光盈盈,庭院裏的花、樹都靜悄悄的,一動不動,像是沉在水底的影子。這時乾隆的心動了一下,那一動,就牽出一項無比浩大的文化工程,乾隆本人和他們身邊的臣工,為這一工程付出了七年的時間。
七年之後,這一重繪《詩經》的藝術工程,才終於在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的酷暑中完成。之後,乾隆興猶未盡,與清宮著名詞臣畫家董邦達合作,共同臨仿了《豳風圖並書》一冊,選用宣德箋金絲闌本行楷書《豳風》詩,又選太子仿箋本,墨畫詩圖,乾隆畫人物,董邦達添上樹石屋舍。
在那漫長的歲月裏,他感到中國書法的巨人在引導着他的手,傳授給他每一筆、每一畫、每一個字中存在的書法秘訣;假如多年後宮廷御醫開列的診斷書可信的話,這種活動在臨摹者和被臨摹者之間,創造了一種催眠的、情感的、愛情的關係,由此,年輕的皇帝總感覺到,自己漸漸滑入了另一個專制君主的皮膚底下;當他把毛筆浸到墨汁中時,毛團便膨脹起來,飽吸了墨汁,精確得跟宋高宗一模一樣。〔參見戴思傑:《無月之夜》,第十一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二○一一年版。〕
繪製《毛詩全圖》,很像今天電影界的經典重拍。馬和之《詩經圖》是一部經典老片,乾隆這位導演,卻執拗地要在他的時代裏為它翻版。但那也不只是被動的翻版,還要清晰地勾勒出王朝的新意。畢竟,時代變了,創作者變了—代替了馬和之的,已是清朝的畫院畫家,代替了宋高宗和宋孝宗的,則是清高宗乾隆—《詩經》中的三百零五首詩,乾隆一個字一個字地抄錄在繪畫的邊緣,甚至在畫稿上,乾隆也不時添上幾筆。唯有他對《詩經》的那一份眷戀與懷念沒有變。七年中,他一筆一筆的描畫和書寫,沒有絲毫的怠惰。那份謹慎與虔敬,與當年的宋高宗和宋孝宗,幾乎一模一樣。
(三)
兩宋之交的皇帝們,無論他們的畫院裏收藏了多少傑出的畫家,也無論他們自己寫出過多少燦爛的書法,他們的名聲都不怎麼好聽,因為身為皇帝,他們丟失了中原的萬里河山,使這個原本立足中原的王朝,永遠地退出了黃河流域,拱手讓給了北方的金朝。這幾乎使它喪失了華夏王朝的正統性(所謂定鼎中原),更不用說南宋後來的空間被越壓越扁,以至於這個王朝與元朝的大決戰竟然在廣東崖山的海面上進行,連中原逐鹿都成了奢望。這場戰事的結局是,一個名叫陸秀夫的忠臣,背着號啕大哭的小皇帝—宋末帝趙昺,縱身跳入大海。在他們身後,南宋的嬪妃和文武百官們也紛紛跳海,變成一堆參差不齊的泡沫。大宋王朝的無限繁華,就這樣被大海抹平。
假如要問責,宋徽宗首當其衝,他一直被視為一個昏庸皇帝與天才藝術家的混合體,宋高宗緊隨其後,因為他軟弱、自私、胸無大志,把這個已經半殘的王朝向火坑裏又推了一把,「中國也正是從那時開始,變得軟弱可欺,惰性十足。」〔范捷:《皇帝也是人—富有個性的大宋天子》,第二百四十八頁,北京:故宮出版社,二○一一年版。〕
這兩位皇帝藝術家造成的悲劇性後果,讓我們不免對藝術的價值產生懷疑—莫非它真是帝國的毒品,誰沾上它,誰就得滅亡?
壯麗而浩大的艮嶽,最終成了埋葬北宋王朝的墳墓,而不可一世的金朝,在把他們從汴京城掠奪的字畫珍玩一車一車地運到金中都以後,也迅速陷入對藝術的痴迷。藝術並沒有提升這個鐵血王朝的精神氣質,相反,卻讓它患上的軟骨病。王朝鼎盛的十二世紀,金章宗邯鄲學步,幾乎處處模仿宋朝。他的世界裏,詩書曲賦琳琅,典章文物粲然,他撫琴叩曲,操弦吟詞,甚至學着宋徽宗的樣子寫起了瘦金體,連他的寵妃,名字都叫李師兒,顯然是在克隆李師師。除了製造上述贋品,他的王朝,也完全翻版了北宋的命運,只不過他沒有成為階下囚,但他的後代,下場卻比宋徽宗還慘—末代皇帝完顏承麟,在公元一二三四年正月的蔡州慌忙登基時,元軍已經殺到了宮門口,完顏承麟潦草地舉辦了即位典禮,就帶着手下將士衝出宮殿,與元軍拚命去了。最終,他拚丟了自己的命,變成宮門處一團血肉模糊的屍體。大金王朝的這位末代皇帝,在位時間不到一個時辰(即兩個小時),成為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帝。
這個金戈鐵馬的王朝,就是在金章宗的手上拐了彎,這帳,不知該不該算在他熱愛的藝術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