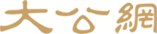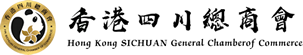【亞洲文旅網訊】“自己穿什麼,什麼就是時尚。他人穿什麼,什麼就不是時尚。”敢這樣口吐狂言的不是哪位如日中天的時尚模特,而是著名作家奧斯卡·王爾德。他從來不是時尚的奴隸,他只制造時尚。在他死後多年,人們仍在熱切討論他的穿衣風格。
但王爾德絕不是唯一一個被寫作耽誤的時裝博主。在《名作家和他們的衣櫥》一書中,曾在多家時尚雜志擔任編輯的特莉·紐曼借80張照片,展示了包括奧斯卡·王爾德、西蒙娜·德·波伏娃和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等50位名作家的時尚品位。
他們的時尚品位暴露了他們的文學品位,他們的著裝態度也絕對是他們的人生態度。
“女性可借助裙子,向社會傳遞她的態度。”能夠這樣賦予裙裝神聖價值的,除了西蒙娜·德·波伏娃,還能有誰呢?
本文節選了《名作家和他們的衣櫥》一書中奧斯卡·王爾德、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菲茨傑拉德夫婦四位的章節,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英]特莉·紐曼
摘編|肖舒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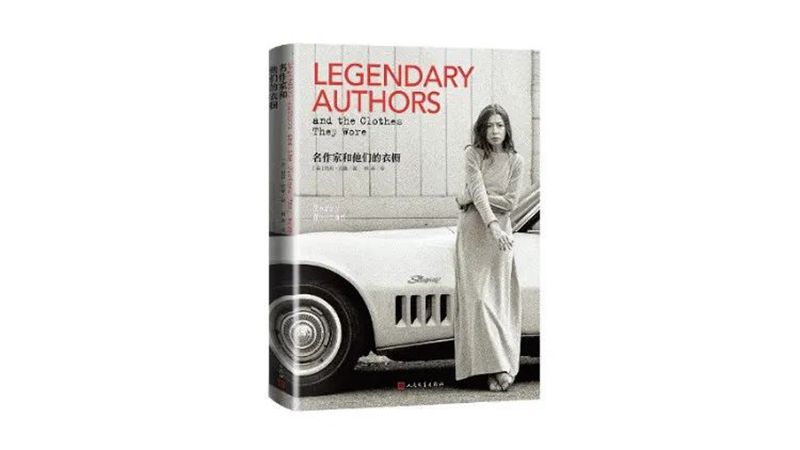
《名作家和他們的衣櫥》,[英]特莉·紐曼著,林燕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7月。
奧斯卡·王爾德
“自己穿什麼,什麼就是時尚。他人穿什麼,什麼就不是時尚。”
——奧斯卡·王爾德,《理想丈夫》,1895年

奧斯卡·王爾德,1882年。
王爾德對服裝的態度,基本上比曆史所表明的更務實。對他來說,這從來不僅僅是種姿態,而是深思熟慮後的觀點。1885年,他在《紐約論壇報》上發表文章《服裝的哲學》,他在文中說:“服裝的美,完全和絕對地取決於它所遮蓋的美,而且取決於它不妨礙自由和行動。”他從來不是時尚的奴隸,他最著名的語錄之一,也來自《論壇報》上的那篇文章,強調了他關於衣裝的思維方式:“時尚是短暫的。藝術是永恒的。的確,到底什麼是時尚呢?時尚不過是醜陋的一種形式,它實在令人難以忍受,所以每隔六個月,我們不得不改變一次!”
王爾德是理性著裝學會的成員,這個學會認為,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緊身衣和裙撐毫無價值。他們斷言,衣服應與實用和美相結合,該協會奮鬥的目標,是把女性從美好年代的荷葉邊和俗麗裝飾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在《服裝的哲學》一文中,王爾德堅持認為,“做得好的服裝是簡單的服裝,從肩部下垂,顯出身體的形狀,皺褶來自穿著它的姑娘的行動……做得不好的服裝是異質衣料刻意造出的結構,衣料先被裁成一片片的,然後用機器縫在一起,最後縫上花邊、蝴蝶結和荷葉邊,以致看上去拙劣,而且昂貴和絕對不適於穿著。”
作為一位真誠的知識分子,再加上在都柏林三一學院和牛津大學受到的一流教育,王爾德能夠通過大量的詩歌和文字,精確地表達出藝術的、深刻的見解。他的著裝理念是他生命流動的延伸,就像他在飯桌上娛樂別人的能力一樣自然。曾有一段時間,他是唯美運動的領軍人物,在倫敦社交界以詼諧機智和生活中的娛樂行家而聞名。他與威爾士親王阿爾伯特·愛德華的情婦莉莉·蘭翠是朋友,1870年代的一個晚上,這位親王不請自來,到王爾德家參加一場降神會,據說還有以下戲言:“我不認識王爾德先生,可要是不認識王爾德先生,別人也就認不得你了。”

奧斯卡·王爾德,1880年前後。
王爾德所代表的唯美運動相信自由、無拘無束的表達,崇尚內在、自然的美,王爾德也徹底踐行了他所竭力鼓吹的一切。在小說《道連·格雷的畫像》的序中,他寫道:“在美好事物中發現醜陋意義,是一種並無可愛之處的墮落。那是一種過錯。在美好事物中發現美好意義的人,是有教養的人,對這些人來說希望是有的。”
1882年,王爾德去了一趟美國,他在此行中的著裝,是他與唯美時尚的戀愛達到的最高潮。1882年的《紐約時報》上有一篇文章,題為《與詩人的十分鐘》,它詳細描述了王爾德奢華的服裝:“他穿一件低領白襯衣,翻開的領子特別大,系一條淡藍色絲綢領巾。他的手放在毛皮襯裏的寬松大衣的口袋裏,頭上包著一條纏頭巾。淺色的燈籠褲、漆皮鞋……左手一根手指上戴的印章戒指,是他展示的唯一珠寶。”王爾德死後幾十年,他的風格仍是人們議論的話題。
王爾德死於巴黎聖日耳曼德佩區的酒店。據報道,他在死前說:“我正和這牆紙決鬥。不是它死,就是我亡。”
關於自己的年齡,王爾德從未說過實話,甚至在1884年的結婚證書上亦是如此——那上面寫著他二十八歲,比他的實際年齡小兩歲。
西蒙娜·德·波伏娃
“盛裝打扮是女性自我陶醉的具體形式;它是制服,又是裝飾;通過這種形式,被剝奪了權利而無法做任何事情的女性,感到她進行了自我表達。”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1949年

西蒙娜·德·波伏娃,1947年。
西蒙娜·德·波伏娃不僅啟發女性從激進的視角思考問題,而且鼓勵她們以激進的視角生活——思考生活,思考她們所穿的衣服,以及這些衣服如何講述了她們和她們對世界的感受。她是存在主義之母,也是披頭族場景的孕育者。德·波伏娃主張摒棄循規蹈矩,主張所有的女性都必須找到藝術的、創新的自我,而且最重要的,是找到理智的自我。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巴黎的知識和藝術精英,包括阿爾貝·加繆和讓·科克托,都聚集在塞納河左岸,討論人生。三十六歲的德·波伏娃是歡樂的中心。然而,在她名震世界的著作《第二性》中,她討論變老的悲哀,不過她在《老年》中繼續說,“如果不想讓老年荒謬拙劣地模仿我們以前的生活,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繼續追求給予我們的存在以意義的目的。”因此,“成熟”並沒有妨礙她與當時只有二十歲的歌手朱麗特·格蕾科等人一起廝混到天明。德·波伏娃喜歡獨具一格,這一核心特性讓她擁有自己的各種時尚選擇。
德·波伏娃在1929年遇到讓-保羅·薩特,當時兩人都在准備哲學教師資格的競爭性考試,它是法國最主要的研究生考試之一。兩人都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參加了這一考試。
迪爾德麗·貝爾在1990年的德·波伏娃傳記中寫道,薩特稱德·波伏娃“衣服穿得不怎麼樣,但長著美麗的藍眼睛”。她當然既是時髦的,又是與時代格格不入的。戰爭期間,總的說來,配額和愛國主義限制了服飾的過度個性化,而在1944年解放巴黎後,時世仍然艱難。如果德·波伏娃的頭發沒有梳成她的那種高高的標志性發髻,她通常也會用戰時流行的環型纏頭巾將它包起來——這是在所有種類的供應都短缺時,婦女保持自己頭發齊整的把戲。當世界開始回歸正常時,這種做法被大多數人拋棄,但德·波伏娃發現這種風格很有用,它成了她形象的一部分。她的披頭族形象的影響之一就是明確實用的樣式也可以很性感。
直到1947年迪奧推出“新風貌”,用他設計的窈窕腰身、性感胸線和質地輕薄的襯裙,奠定了1950年代女性的倩影,時尚才再次成為真正的聚焦點。在當時,它是對戰爭匱乏年代的理想解藥。在《第二性》(1949)中,德·波伏娃宣稱,“最不實用的禮服和禮服鞋、最嬌貴的帽子和長襪都是最優雅的”,而迪奧和他的服飾代表了桎梏“他者”的枷鎖。她更喜歡我行我素,正是這種態度,不斷吸引自由放任的披頭族王國以相似的精神擁抱她的思維方式。

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讓-保羅·薩特在裏約熱內盧的科帕卡巴納海灘,1960年。
在她最受推崇的著作《第二性》中,德·波伏娃探討了為何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從屬於男性。她寫到男性對女性的表述,也寫到女性對女性的物化。特別迷人的一點是她激烈的反時尚熱情。她談到,對女性來說,“在乎自己的美麗,盛裝打扮,是一種工作”。西蒙娜願意自己來做“時尚工作”,她從來都是把指甲修得精致,塗著指甲油,曾穿著貂皮大衣參加支持墮胎的遊行,還在1947年的《紐約客》上,被珍妮特·弗蘭納1和斯坦利·埃德加·海曼2描繪成“你見過的最漂亮的存在主義者;而且熱切,溫柔……謙遜”。
在《第二性》中,德·波伏娃承認,“女性可借助裙子,向社會傳遞她的態度”,雖然在當時,她爭辯說這帶有壓迫性質,但在今天,這被看作是一種藝術選擇。無論是穿著,還是形象,德·波伏娃都是智慧的;穿百褶裙,系絲質領結去授課,她看上去精明強幹;穿貂皮大衣,坐在花神咖啡館,她看上去雍容華貴;在家裏,穿一身量身定做的天鵝絨套裝,她看上去美麗自然。無論她選擇穿什麼,都並不是重要的。正是這一事實具有內在的吸引力,而且是追時髦的人至今仍在追求的精髓。
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和澤爾達·菲茨傑拉德
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和澤爾達·菲茨傑拉德是無數崇拜者心中的時尚偶像,而其中還有許多人,可能從未讀過他們兩人的任何作品:這足以說明他們的名聲之大。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的試金石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曾數度被改編成電影。巴茲·魯赫曼12013年的版本,捕捉到了那個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十年的華麗色彩。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筆下故事的結構,是導演和設計師們的夢想;敘述菲茨傑拉德夫婦的生活和作品,具有魔幻般和悲劇般的魅力,電影界和時裝界從不會對此感到厭倦。2011年,凱特·摩絲2的婚禮受到澤爾達的啟發,英國版《時尚》為其刊登了十八頁照片;她的婚紗禮服是1920年代式斜裁,她所戴的傳統戒指,是澤爾達和斯科特婚戒的翻版。

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和澤爾達·菲茨傑拉德在法國蔚藍海岸,1926年。
菲茨傑拉德夫婦過著速朽、輕佻的生活——他們花錢如流水,全年都在度假,毀壞酒店房間,整天爛醉如泥,跳舞,隨隨便便與朋友斷交。他們的生存方式最終毀滅了自己。他們的時尚理念成為一個崇尚華麗和揮霍的時代的象征。
澤爾達1920年去紐約結婚前,過著南方美女的輕松生活。她帶著一箱薄紗連衣裙和絲絨休閑長褲來到紐約。斯科特·菲茨傑拉德認定她需要更時髦的打扮。他讓她跟隨自己的老友瑪麗·赫希去采買,後者領她見識了法國設計師讓·巴度輕松的時尚、簡潔的設計和完全現代而修長的輪廓。沒過多久,澤爾達的都市衣櫥成形了,小城長褲被徹底拋棄。她的卷曲短發燙成完美的波浪型,身穿鑲亮片和毛皮的禮服出席派對,那些禮服的剪裁讓她看上去像四季豆一樣苗條,還襯出讓人豔羨的平胸。斯科特則幾乎一向身著三件套花呢西裝,系領帶,口袋裏放著手帕;時髦的中分頭塗了發蠟,更凸顯他那種熒屏俊男的魅力。如同時尚形成他們的性格,幫助他們炫耀想要吸引世界注意的東西,時尚在他們的寫作中也同樣發揮了作用,其中情緒和個性與服裝的描寫有著微妙的平行關系。要了解菲茨傑拉德首創的“爵士時代”一詞,時尚是關鍵。1925年,《了不起的蓋茨比》在滿目頹廢墮落中出版,快活、渴望、
煌和憂鬱是該書的所有中心主題。那是一個被菲茨傑拉德夫婦人格化的時刻。

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和澤爾達·菲茨傑拉德,1921年。
厭世、美麗和富有,是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筆下有教養人群存在的目的。他描寫毀滅的和神聖的。激情、炫耀、金錢和災難是他筆下故事的招牌元素。澤爾達在城裏亂跑,跳進華盛頓廣場的噴泉,與丈夫之外的男人調情,同時在皮草和香檳上大肆揮霍,這已經成為1920年代漫畫的標配。
但在現實中,澤爾達和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的生活是災難性的夢魘。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四十四歲在好萊塢突發心髒病去世,那時他正努力當個編劇,並試圖寫完最後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末代大亨的情緣》。澤爾達四十七歲殞命於北卡羅來納州阿什維爾高地醫院的一場火災,當時她正在那裏接受精神病治療。兩人最後都未能活到頤享天年: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從不認為自己作為作家留下了什麼遺產,澤爾達則對自己的命運心灰意冷,這加重了她的精神疾病。
在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的小說《人間天堂》裏,他的自傳性主角艾莫裏·布萊恩證實了作者擁有的一些虛有其表的自我價值。“油頭粉面”這一人格面具的人生哲學和風格,正是斯科特在現實世界中的追求。而這一人格面具在小說中的定義,絕對酷似他本人:“他衣著講究,外表整潔,這個名稱肯定來源於短發中分,油光水滑,循著時髦樣式向後梳攏。”